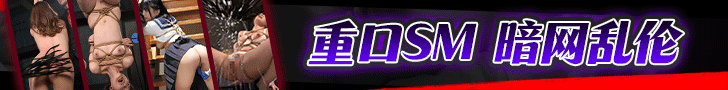53
他要把所有说不出口的情愫都用性爱塞进我的身体里似的,激亢的撞的更深。
穴口被完全捅开了,内部又麻又热,说不上特别舒服,只是酸的要命。
我却忍不住笑了起来,被他压在身下,也仿佛踩在了他的头上,高兴的笑出了声,断断续续的恨恨说着刺激他的话。
“孟知礼比你成熟比你、比你优秀哈你说”
嘴唇被猛地捂住了,要闷死我似的。
他好似不愿意再从我口中听到任何关于孟知礼的好话,眼里瞪出血丝,吃人般的死死盯着我,愤怒的神情里夹杂了一丝真切的难受。
迎上我直勾勾的视线,他仿佛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狼狈的扭头避了一下,然后手掌移到我的眼上,不准我再看他。
嘴唇被他堵住了,热情的舌头非要从肌肤相贴的极致亲密中来找回某种挫败的自尊心。
一条腿被抬了起来,搭在他的肩上,两具滚烫的身体嵌的更深了一些。
穴口被鞭挞的发红,又爽又胀,我的性器被他的小腹压着蹭,哆哆嗦嗦的射到什么也吐不出来,稍微碰一下就有种火辣辣的疼。
“孟知呜!”
我实在吃不消他狂风骤雨般的高频率冲撞,胯骨被撞的发热,下半身都要失去知觉了,勉强从唇齿交融的间隙里拼命吞咽着口水,哭的尾音颤抖。
“不要,不要了——”
孟知佑不听,又把我的舌尖吮的发肿。
炙热而凶猛的精壮身体将我困在床底之地,喘的犹如一匹被彻底激怒的野兽。
“不准喜欢哥,不准喜欢孟知礼!”
叫到孟知礼的名字时,发狠的语气里漫出晦暗的负面情绪。
我是该欣喜,该欣喜于成功分裂了他们两个兄弟,可眼下我只顾着躲,只顾着求他,满脸泪水的呜呜咽咽。
他用力吻着我的嘴唇,说话时,翕动的柔软嘴唇挤着我的面颊,激动的威胁语气听起来居然如同在恳求。
“你要喜欢我。”
过于强烈的撞击让我的小腹猛地一酸,脚趾使劲蜷缩着。
我后知后觉的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腥臊味。
我失禁了。
尿水溅在了摩擦的小腹之间,孟知佑也浑然不觉般,只盯着我,指节用力掐着我的颊骨,十分不稳定的语气残酷又脆弱。
“鸦鸦,说你喜欢我,只喜欢我,不然我把你操的尿都尿不出来。”
难堪爬满了我涨红的面颊,一股股的尿液还在从顶端溢出,我急促的哭着,实在怕他会做出这样让我崩溃的事,只能哽咽着妥协。
“喜欢、喜欢你”
尽管不清楚真假,但孟知佑依然得到了他想要的。
阴霾一下子被吹散了,排山倒海的喜悦如同打了胜仗,他扬眉吐气,得意洋洋的抵着我的鼻尖,目光灼灼的纠正。
“说错了,是只喜欢我,最喜欢我。”
我依言说出了他想要的回答,难耐的试图并拢双腿,求他停下来。
但他陡然高亢起来的情绪比刚才还要磨人,不顾我的哀求,硬是捅的我腿根痉挛,穴口的嫩肉几乎要热的融化掉。
我浸在腥膻与腥臊的液体里,迷迷糊糊累的昏睡了过去,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才停下的。
第二天睡到了中午我才醒来,昏暗的遮光窗帘营造出了缱绻温情的氛围。
我觉得脸颊有些痒,下意识抬手挠了挠,随即热乎乎的嘴唇又印了上来。
孟知佑一手穿过我的颈后揽着,一手圈着我的腰,精神奕奕的笑着说,“鸦鸦,该起床了。”
我筋疲力尽,浑身还软的像一滩水,动也不肯动,只又往被窝里埋了埋,重新陷入令人安心的昏暗里。
孟知佑笑了一下,笑声格外愉悦。
他轻轻顺着我的长发,轻声嘟囔了一句“小懒猪”。
温柔到不可思议的声音钻进了我混沌的梦里,被分解成无法理解的朦胧碎片,然后无声的蒸发。
片刻,他轻手轻脚的离开了被窝,替我掖好被角,又眷恋的亲了一下我的额头,就静悄悄的走了出去。
而我一直睡到了下午才渐渐醒来。
饿的饥肠辘辘,我又赖了一会儿床,撑着打颤的双腿勉强去冲洗了一下,又疲软的坐回到床上,拨通了楼下厨房的电话,说想吃面。
很快,有人开门走了进来。
不是佣人,是孟知佑。
他见我蜷缩在还算干净的床脚,不愿意碰一片狼藉的被褥,于是找来睡衣给我披上,将我抱了起来,让佣人进来更换床单和被褥。
更多的人走了进来,虽然很安静,但也无法忽视掉存在感。
我不得不难堪的伏在孟知佑的怀里,闭眼听着他的心跳声,浑厚有力,和手臂一样将我安置在离他最近的地方。
他显然很喜欢我这副难得没有挣扎
的温顺姿态,低笑着说,“鸦鸦好乖。”
换好床单,佣人们安静的退了出去,厨房的佣人将新鲜的素食面端到了床上的小桌子上。
孟知佑这才放下我,在一旁看着我吃完后,恢复了些精力,才问。
“鸦鸦还要睡吗?”
我摇了摇头,声音嘶哑,“不睡了。”
他点点头,抬手将我领口的扣子一颗颗系上,专心致志的目光充满了温情的亲昵,恢复如常的少年面容依然盈着天之骄子的矜贵与骄纵,一如既往般的无懈可击。
可我见识过了他昨晚的狂态。
我知道,我能伤害他。
54
孟知佑抱我出了卧室。
我不想这样依赖他,但实在走不了路。
而出门后看到刚走进一楼门口的孟知礼望过来的目光,我一下子就不挣扎了,乖顺的搂着孟知佑的脖颈,垂眼看着孟知礼。
孟知礼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提着一个公文包,对他毕恭毕敬的。
心里猛地一跳,我大概猜到了他的身份。
孟知礼走上楼梯,一直看着我,站定后才看向孟知佑,淡淡的说,“去书房吧。”
跟过来的那个男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沓需要签字的材料,我瞥了一眼,最上面是一个英国学校的全称。
我没说话,只木着脸坐在孟知佑的怀里。
男人将早就准备好的材料分成了三份,孟知礼将每张都翻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了,然后把签字笔推到我面前。
“鸦鸦,签字。”
他也不解释,仿佛知道我一定能看得出来眼下是什么情况。
那双漆黑的眼眸紧紧盯着我,似乎在准备着我的任何反应,无论是大吵一架还是歇斯底里,他都绝对能压制住我的一切反抗。
他们毁约了,并且毫不愧疚。
短暂的静寂中,孟知佑把桌上的签字笔塞到了我手里,真以为我是任由他们操控的玩偶似的,语气轻松的笑着哄道。
“鸦鸦,签了字,晚上我们一起看电影好不好?”
他在试图用另一件事遮掩住当下的凝重,将签了这些留学材料尽量放到最轻微的分量上,让我无从察觉,并且顺从听话的如了他们的意。
攥着签字笔的指节被硌的发痛,我僵着一张脸,能感觉到他们都在盯着我。
以一种警觉而狐疑的,不动声色的打量与审视,笃定了在掌控范围之内的上位者姿态盯着我,将我逼到捕兽网,逼到无路可退的角落。
我慢慢抬起手,手肘抵着桌沿,一张一张的签上自己的名字。
薄薄的纸张力透纸背,几乎要被浓重的黑色名字割裂成碎片。
看到我一声不吭的签了字,他们无声的松了口气,压在我身上的沉甸甸的凝视变得轻盈起来。
也许他们心里在想,我怎么可能会不签字呢。
进入富贵的孟家,去英国留学,这是多少贫苦家庭梦寐以求的平坦人生。
他们以为我在这一年里已经逐渐适应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生活,自然不会拒绝留学的诱惑,不会拒绝和他们站在同样高度的位置上。
一年之约算什么,他们不提起,我不在意,那么这个约定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们也各自签好了自己的那份,男人将材料小心翼翼的收回公文包,退了出去。
书房的氛围变得无比和谐,如同卸下了心头的重担,连孟知礼也露出了明显的笑意,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脸,声音极其温和。
“想看什么电影?”
我还在盯着空荡荡的深色桌子,竭力维持着脸色的如常,“随便吧。”
影音室的隔音很好,他们挑了一部同性的爱情片。
外国人用含情脉脉的腔调诉说着彼此的爱意,年轻美丽的情人在暮色下接吻。
他们看的很入神,一人一边拉着我的手,我盖着小毯子,面无表情的盯着巨大的屏幕。
目光是虚的,我根本就没有在看,犹如在煮沸的水里不断弹跳,试图跃出这濒死的牢笼,一颗心变得焦灼难安,要用力咬着牙才能不发出不堪重负的绝望呻吟。
肩膀被亲密的抵着,少年的温度从皮肤传来,可我只觉得周身发寒,止不住的想发抖。
孟知礼忽然偏头看了我一眼,稍稍凑近,面容的轮廓遮住电影屏幕,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他的声音很轻,近乎温柔,“怎么哭了?”
听到这句话,另一边的孟知佑也扭过头,有些吃惊,继而大笑了起来,“这部电影的确拍的很不错,鸦鸦居然看哭了,哈哈哈。”
不知怎么的,孟知礼凑近来舔我的眼泪,孟知佑见状也握紧我的手,不甘示弱的从毯子下面摸进我的睡衣里。
昨天使用过度的穴口还很湿软,轻易的容纳进了勃发的器官。
大概是我签字就是默认了答应和他们一起留学这件事让他们非常满意,确认了我的归属权
就要尽情的享用,被冷落的孟知佑没忍住,也插了进来。
尚且还泛着酸麻的穴肉哆哆嗦嗦的被撑开,吃力的吞着两根近乎一模一样的阴茎,我胀的直哭,微弱的喊着不要。
但挣扎的双手被牢牢捉住了,后腰的腰窝也被掐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道拖着我往下坐到他们要杀了我的腥膻器官上。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钝痛,腹部微鼓,我撑的想吐,浑身冒冷汗。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他们越来越热的身体与目光。
这次没来得及用他们一向喜爱的手段,没有绳子,没有玩具,没有马鞭,只有最原始的欲望从青涩的少年身体里疯狂的涌出来,将我淹没。
影音室的沙发宽敞柔软,我被顶的跪都跪不住,东倒西歪的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之间摇晃,拖着哭腔哀求。